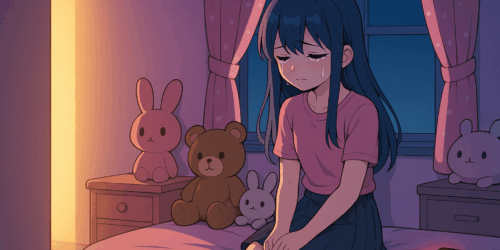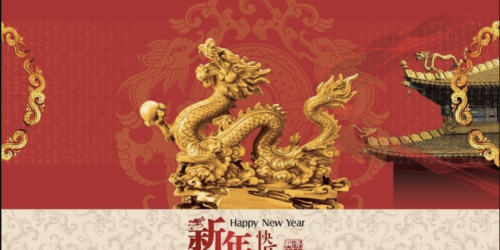地雷系文化的发生与变形:边缘认同的生成机制与社会结构批判
※本文由生成式AI辅助写作,作者仅进行了简易的事实筛查,不保证100%正确,仅供参考。请勿作为权威信源使用。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犯到贵司的著作权请联络本人本人定在规定时间内妥善处理。

Left half: A cute girl in “Jirai-kei” (地雷系) fashion with dramatic makeup, twin tails, black-and-pink frilly outfit, and platform shoes is walking casually on a brightly lit street in Shinjuku Kabukicho at night. She’s holding a tall can of strong lemon-flavored shochu (Strong Zero style). Neon lights and colorful signage glow behind her.
Right half: In a cyberpunk-lit room with LED strip lighting and multiple monitors, a male streamer wearing a sailor-style school uniform and cat-ear headphones is livestreaming. He looks feminine, with soft makeup and an expressive face, surrounded by chat messages on screen.
Hyper-detailed textures, ambient glow, depth of field, Japanese urban atmosphere, rich lighting contrast, high-resolution cinematic framing
引言
在这个自我可被剪辑、标签可被下载、痛苦可被表演的时代,我们究竟如何定义‘我是谁’?
在以“地雷系”“男の娘”“虚拟Vtuber”以及“魔爪文化”等符号所构成的当代边缘文化现象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存在方式:他们在社会的边缘地带,不断以表演性的方式试图建构可被确认的自我认同。这种行为并非简单的风格选择,而是在深层回应着现代社会广泛蔓延的**“意义的枯竭”(meaning collapse)与身份结构的断裂**。
个体不再能依靠传统路径(家庭、性别、阶层、信仰)来确认其存在位置;同时,在社交媒体与算法主导的拟像空间中,他们也面临着被快速消费、误读甚至娱乐化的命运。
在这篇论文中,笔者试图跨越文化史、社会结构、性别理论与媒介机制多个维度,从“起源—演变—当下—展望”四个层级出发,对当代边缘文化中自我认同的演出机制进行结构性分析,并追问:
- 是什么迫使一群人只能靠“病娇滤镜”“标签美学”才能活下去?
- 为什么现代社会在道义上宣称“尊重多样性”,但制度上却几乎不给出一条“第三条路”?
- 我们,作为观看者、分析者、共时代者,是否可能发展出一种既非猎奇,亦非同情的伦理参与方式?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承认:
理解是一种承认,参与是一种共振,改变是一种缓慢的共同生成。
一、起源:表演性自我建构的历史脉络
日本边缘文化的表演性传统。 在江户时代的日本社会,存在一套由边缘角色通过“表演性自我建构”来回应主流规范的传统脉络。例如,花魁(高级游女)以精心设计的仪态和服饰扮演着理想化女性的角色,她们的人格由其地位和观众期待共同塑造。同样地,武士阶层流行的若众道(即“众道”,指武士与美少年之间的男色之爱)也形成了一种角色扮演的文化:美少年(若众)往往蓄特定的发式、衣饰以扮演被崇拜的艳丽形象,而年长武士则在这一关系中扮演保护者和导师。这些角色超出主流家庭和生产角色,本质上是对身份的表演性重构。个人通过扮演社会赋予的特殊身份,获取一定程度的认可和叙事意义。这与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拟剧理论”不谋而合:戈夫曼认为日常社会互动如同舞台表演,每个人在特定场合按照社会期待呈现出一个角色,以影响他人对自己的印象。在江户的风俗场域中,花魁和若众的角色正是这种角色扮演的范例。他们在前台极力表现出社会期望的形象,而真实自我则隐匿于后台。
“边缘角色 × 表演行为 × 社会叙事”结构的雏形。 德川幕府时期,上述边缘角色通过表演行为融入社会叙事,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结构雏形。一方面,这些角色处于社会的边缘地带(例如青楼、若众道圈子),不属于普通家庭或职业序列;另一方面,他们的存在被社会准许并凝视,成为艺术创作和大众想象的对象。例如,浮世绘和文学作品中频繁描绘花魁、歌舞伎役者和男色美少年,将其塑造成那个时代都市文化的一部分。这种**“边缘角色—表演—叙事”的循环,意味着边缘人物通过精心扮演特定形象,为主流社会提供了投射欲望与反思秩序的象征窗口。在这一过程中,自我不再是内在本质,而更像是悬挂各种表演形式的“衣帽钩”——个体被社会赋予的角色和剧本所操控,自身变成了承载符号的载体。正如学者所评述的,戈夫曼笔下的表演性视角中,个人“仿佛是受社会和文化操控的傀儡”,其展演的并非真实自我,而是他人眼中期望的自我形象。这种对主体能动性的消解预示了此结构下个体身份的脆弱性**:自我被角色表演吞没,真实主体逐渐隐退于符号化的戏剧中。
明治维新与现代性断裂下的身份焦虑。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迅速引入西方现代体制和价值观,引发了传统身份体系的断裂。原有的边缘角色体系被打破:武士阶层废止、青楼制度受抑制,社会开始推行维多利亚式道德和两性规范。这种急剧转型带来了身份认同的集体焦虑。明治-大正时期的文化作品中可窥见早期症候:森鸥外、永井荷风等作家的作品往往描绘旧封建欲望与新道德观的冲突,充满对现代都市中迷失自我的叹惋。女性开始进入学校形成女学生文化,由此衍生出被称为“S关系”的亲密同性爱友谊风尚。当时的女学生被赋予浪漫化的形象(如袴制服、手捧名著的知性少女),她们之间的友情带有表演色彩地被文学作品(如吉屋信子等人笔下的小说)加以颂扬。然而这些理想化叙事背后,是女性角色定位在传统贞淑妻子与新式独立女性之间的游移不定——身份的不稳定催生出以浪漫友情为逃避的角色扮演。同一时期,男性中出现耽美派文学思潮(“耽美”意为沉溺于美),谷崎润一郎、泉鏡花等作家提倡唯美颓废的审美,塑造阴郁而中性的青年形象以反抗明治社会日益功利、刚健的阳刚价值。这可被视作边缘身份的文艺表达:通过对中性美少年的迷恋和感官享乐的描写,耽美派试图表演一种与主流阳刚身份决裂的自我。同样地,大正末期的摩登女郎(モダンガール)现象,则是女性以西式洋装、短发、出入舞厅的形象出现,颠覆了传统妇德——摩登女郎既是真实的新兴都市女性群体,也是媒体塑造的表演性符号,折射出社会对女性解放的憧憬与恐惧。这些早期现代的边缘文化现象,都是传统角色断裂后的身份焦虑之表现:个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新的定位,只得通过表演某种极端化身份来暂时缓解这种焦虑。这印证了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性别表演理论:性别气质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社会**“脚本”下被不断重复建构出来的。一代代人沿袭并强化关于男性气概和女性气质的剧本,将其误认为自然本质。明治以来日本的身份变迁剧烈,使得许多人有意识地扮演某种脚本(无论是浪漫女学生还是颓废美少年**),以寻求一个可接受的身份位置。这种对权威规范的反叛和重复脚本的扮演,同构出近代日本边缘认同的雏形。
二、演变:亚文化化与符号商品化的进程
昭和至平成:边缘文化的亚文化化。 二战后的日本,高度经济成长和社会规范的重建并未消弭青少年的叛逆心态,反而催生出一系列自成体系的亚文化。20世纪50年代,城市底层青年和愤世嫉俗的无业游民形成愚连队(ぐれんたい)群体,这是战后不良少年文化的滥觞。愚连队成员衣着夸张、结伙飙车闹事,以暴力和义气挑战社会秩序。到60-70年代,不良文化进一步在校园蔓延,出现**“不良少女”及其组织化形式女番长**(スケバン,即少女帮派首领)。据报道,1960年代中期开始各地兴起少女暴走团伙;到1970年代,女番长帮派蔓延并升级,其成员从最初只是校内抽烟逃课的少女发展到实施打架、商店行窃等严重不良行为,甚至形成跨地域的大型联盟。例如,东京曾有多达80人的少女盗窃团伙,而关东地区据称出现过拥有约两万名成员的“女性犯罪联盟”。这些不良少女群体以特殊的穿着和行事风格与主流青春范式对抗:典型形象是身着水手服或改造校服,留长染发,佩戴匕首等夸张饰物,以示与循规蹈矩的“好学生”决裂。在媒介再现中,不良少女形象一方面被妖魔化为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又成为通俗文化中的迷人反英雄(如漫画《スケバン刑事》及一系列东映的“女番长”映画)。通过媒体,不良亚文化进一步符号化:皮裙、长靴、烟头、纹身等符码被固化为“不良少女”的标签。这标志着日本边缘认同开始形成亚文化圈层,并被主流社会以类型化方式加以注视和消费。
符号的商品化与消费社会的侵入。 伴随80-90年代日本消费社会的繁荣,许多原属地下的亚文化符号被商业市场收编,成为可售卖的时尚。典型案例是1990年代中期兴起的コギャル(Kogal)文化。这一亚文化最初由涉谷地区的女高中生发起:她们违反校规将制服改造成迷你裙,染金发、晒古铜皮肤,穿厚底鞋,在街头嬉游。这种“不良少女”新变种带有反叛色彩,但很快被时尚和媒体捕捉包装为潮流。杂志和电视塑造出“Kogal偶像”,商业品牌推出专门面向コギャル族群的服装系列,大受少女追捧。据记录,当时出现了一批日本本土服装品牌以夸张可爱的风格来迎合Kogal审美,并获得热烈反响。消费资本将亚文化的标志(如超短裙、松糕鞋、坠饰手机壳等)转化为流行商品,使得反叛的符号变成商家逐利的时尚卖点。更有甚者,Kogal文化催生出灰色的符号交易:一些Kogal女孩为了获取名牌服饰和娱乐资金而从事“援助交际”(即与年长男性约会获取金钱报酬)。到1994年前后,日本高中女生卖春现象激增,其中相当比例是穿着时髦的Kogal。有观察指出,“Kogal”一词一度在海外被直接与东瀛青少年性交易画上等号,因为不少女孩以牺牲肉体来满足消费欲望。这表明边缘亚文化已经被深度商品化:叛逆身份本身成为消费驱动的角色,人格认同被市场逻辑渗透,其价值以能否转化为流量和货币来衡量。
新兴亚文化形态的崛起。 进入平成末期与令和初期(约1990年代末至2010年代),互联网和动漫游戏文化兴盛,派生出更多样的新亚文化形态,丰富了边缘认同的谱系。其中一类是以精神疾病意象和过激情感为美学核心的病娇美学。所谓“病娇”(ヤンデレ)原指动漫中对爱情病态执着、外表娇弱内心阴暗的角色类型,而在现实青年文化中,衍生出**“病态可爱”(病みかわいい)的审美风潮:年轻人(多为少女)用绷带、药丸图案、针管等象征心理创伤或自我毁伤的元素搭配洛丽塔风或娃娃风的可爱服饰,形成诡异又甜美的视觉反差。这种风格背后的认同机制是:以外在的病态符号来表达内心的绝望和求爱欲望,从而在同好圈子内获得理解和认可。同期出现的“男の娘”(即“伪娘”)文化,则是生理男性通过女装和萌态扮演可爱的女性角色。这既是对传统性别角色的反叛,也是御宅族亚文化内部自我消解、追求另类性的表现——男性扮演的“女孩”角色往往带有夸张的萌属性,仿佛“女性”本身也成为了一种可以表演和消费的符号。巴特勒的表演性理论认为,性别身份并非恒定不变,而是在不断重复的行为中被生产出来。“男の娘”现象正体现了这一点:通过跨性别的日常表演,参与者生成了一种新的性别角色**,挑战了二元性别规范。又例如,近年来在青年网络社区中流行的所谓**“药系文学”,指的是围绕药物滥用、精神科药物体验和心理疾病自述的一类文字创作。许多年轻人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过量服药(OD)的经验、失眠抑郁的感受**,甚至把各类处方药物当作角色来描绘——这一现象可以视作传统“颓废文学”的当代翻版,以文字形式构筑出病态浪漫的自我形象。虎嗅网的报道揭示,在这些圈子中,不少青少年比拼谁尝试过更多精神科药物、谁吞服剂量更惊人,有人炫耀一次吞下几十片舍曲林(抗抑郁药)。这种对药物的迷恋和叙事,实则是将真实的生理创伤转化为一种叙事资本:通过“药物—症状”的叙事来建构身份,在亚文化团体中博取认同。这些新兴形态(病娇审美、男扮女装、药物文学等)的共同点在于:角色即疗伤——通过扮演或叙述一个极端化的身份,个体寻求将内心的边缘感合法化、常态化,在同类圈层中获得心理庇护。
情绪性道具与身份建构。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亚文化演变中,一些商业商品被赋予特殊的情感符号,成为边缘认同者建构自我的“情绪性道具”。以能量饮料**“魔爪” (Monster Energy)为例,它在边缘亚文化——尤其是“地雷系”或Menhera人群中扮演了标志性道具的角色。对普通人而言,魔爪饮料不过是提神饮品;但在地雷系少女的社交媒体照片里,一罐罐颜色亮丽的魔爪却频繁出现,成为她们身份风格的一部分。粉色罐装的魔爪尤其受到青睐,被视为“地雷系最爱”。究其缘由,一方面,魔爪所含的高咖啡因迎合了这些少男少女的生理需求:许多沉迷夜生活或深陷抑郁失眠的地雷少女以魔爪提神和代餐**,甚至把高剂量咖啡因当作廉价合法的兴奋剂。一罐355ml的魔爪含咖啡因93毫克,是红牛的两倍;有的“进阶版”地雷少女还会一边灌魔爪一边服用来路不明的药片,以追求迅速麻痹神经、达到亢奋的效果,从而让自己营造出的“厌世病娇”人设更加稳定持久。另一方面,从符号角度看,魔爪那张扬的包装与“不健康”形象恰恰贴合了边缘亚文化对反主流、颓废美学的追求——拿着粉红魔爪自拍,已成为在同辈中表明“我属于地雷系圈子”的宣示方式之一。这类消费品符号化的现象,呼应了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对消费社会的批判:消费不仅满足物质需要,更通过符号赋义来建立区隔和身份认同。对于边缘群体而言,一罐魔爪饮料、一个特定品牌的打火机抑或一款风格怪诞的玩偶,都可能成为情绪投射的道具,帮助他们扮演某种身份角色并从中获得心理慰藉。商品的符号功能被发挥到极致:物品不再是物品,而是自我表演的道具、情绪寄托的容器。边缘青少年通过占有和展示这些道具,完成对自身边缘身份的再确认。
三、当下:地雷系文化的符号结构与话语角力
地雷系的符号结构:视觉自我演出的逻辑。 进入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当下时代,日本出现了引人瞩目的**“地雷系”文化**(日语称“じらい系”)。“地雷系女子”这个概念源自网络,用以描述一类外表可爱甜美、内在情绪不稳定的年轻女性。她们被比作“地雷”,因为相处初期楚楚可怜、惹人怜爱,一旦深交却可能因为极端的爱恨而让对方“踩雷”受伤。这一人设本质上是二次元“病娇”形象的现实投影:娇小柔弱的身体+难以预测的攻击性。在符号层面,地雷系女孩有一套高度程式化的视觉符码。典型装束包括:柔顺的黑色或浅色长直发,略显病态苍白的妆容,大直径美瞳制造的水汪汪“下垂眼”,脸颊上的过量腮红营造哭过般的脆弱神情,再辅以与甜美服饰形成强烈反差的面部穿刺或锁骨纹身。服装偏好黑色蕾丝、泡泡袖、哥特萝莉风,配饰常见颈圈、银饰链条等。她们在Instagram、TikTok等平台发布的照片往往经过精心摆拍和过度修图——锥子脸、巨眼、小巧下巴、惨白滤镜是标配。这套符号系统具有鲜明的戏剧张力:一方面是可爱与美的极端放大,另一方面又植入死亡、颓废的暗示,从而营造**“人畜无害的外表+随时爆发的阴暗面”这一反差效果。地雷系文化充分利用了社交媒体“以眼球经济衡量一切”的逻辑:在影像传播的平台上,夸张的视觉符号能赢得更多关注和点赞,因而地雷少女们不断强化自己的造型剧目,在数字舞台上扮演这一脆弱又危险的角色。这种自我演出高度印证了戈夫曼提出的“印象管理”艺术,只不过前台已从线下移至线上,而表演技术也升级为美颜滤镜和图像编辑。个体的自我认同几乎完全通过网络观众的反馈来塑造,“看见即存在”**成为地雷系一代的生存信条。在此意义上,地雷系的符号实践也延续了日本边缘文化中“以表演寻求身份”的传统,只是媒介从江户时代的浮世绘茶屋变成了令和时代的社交媒体矩阵。
虚拟身份与现实创伤的交错:角色即庇护所。 当下的边缘文化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面向,是虚拟身份为创伤主体提供庇护的现象。虚拟YouTuber(Vtuber)的流行便是典型一例:越来越多现实中感到孤独或受伤的年轻人,通过一个卡通化的虚拟形象在网络世界“重生”,扮演主播、歌手等角色,对外呈现与真实相去甚远的性格与故事。虚拟身份的魅力在于匿名性与可塑性:个体可以抛却现实中的姓名、外貌、社会背景,重新以理想化的人设示人。这对于那些有心理创伤或强烈边缘感的人来说,无疑充满诱惑——现实中备受欺凌的宅男可以化身为可爱的二次元美少女形象来和观众互动,抑郁内向的少女可以扮演活泼治愈系的虚拟偶像来获得粉丝的爱戴。虚拟角色成为他们的心理避难所,一个精心设计的“面具”用以隐藏脆弱的本我。在这个过程中,“角色”既是创伤的遮罩,又反过来滋养了扮演者:通过饰演理想化的人物,他们在虚拟空间里得到现实中渴望却不得的肯定和关注,从而缓解孤独与自我否定。然而,这种虚实交错的身份实践也潜藏风险:当角色成为主要的自我价值来源时,扮演者可能进一步疏离现实,更难以直面真实的自己和问题。如果虚拟人设崩塌(例如不慎曝光真实身份或引发负面舆论),反而可能让当事人遭受二次打击。尽管如此,虚拟身份现象仍揭示出现代边缘认同的一种自我疗愈机制:个人通过主动的角色扮演,在想象空间中重构自我 narrative,进而获得情感寄托。其背后可以借鉴精神分析和性别理论的视角:正如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指出人靠想象的他者来认知自身,边缘青年也在虚拟镜像中寻找一个理想自我,以修补现实中的裂痕。
主流话语对边缘表达的规训与污名。 地雷系等边缘文化在受到部分青年追捧的同时,也面临来自大众话语的强大压力。主流媒体和社会舆论往往通过简化、污名化或娱乐化的方式来描绘这些边缘群体,从而达到社会控制之效。这种过程类似于福柯(Michel Foucault)所阐述的话语-权力机制:主流话语拥有定义何为“正常”或“异常”的权力,将边缘表达置于特定框架下加以管理。具体而言,媒体常以猎奇或惊惧的口吻报道地雷系现象,突出其中荒诞极端的一面,例如夸大个别少女自残、滥交的行为,以将整个群体刻画为“精神异常”者。这种路径化叙事掩盖了边缘亚文化产生的社会背景(如家庭失功能、教育压抑等结构性因素),将之归因于个人心理问题,从而为社会合法化“矫正”干预提供依据——例如鼓吹加强网络内容监管、要求家长学校严加管教等。有研究者指出,社交媒体固然放大了青少年亚文化的影响力,但现代性本身所带来的疏离和焦虑才是深层诱因。然而大众舆论往往归咎于媒介或个体道德沦丧,这实则是对结构性压抑的遮蔽,使主流社会无须反思自身的问题,而将矛头对准边缘群体本身。另一方面,娱乐工业则倾向于消费化边缘文化,将其元素抽离原本的反叛语境,转化为无害的流行符号。例如,“病娇”形象通过动漫游戏的大众化,变成御宅族喜爱的萌属性,原本蕴含的对于亲密关系病态依赖的批判意味被冲淡;不良少女、哥特萝莉等形象频繁出现在时尚杂志和偶像MV中,只作为猎奇卖点,被审美地中性化。根据戈夫曼的污名理论,社会会通过贴标签和刻板印象来界定与排斥“异类”。污名化过程将复杂的人群简单化为几个负面特征(如“精神不稳定”“不爱惜身体”),这样的标签既在公众中制造恐惧和偏见,又在边缘群体自身中内化为自我认知的一部分,强化其与主流的隔阂。这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规训:通过话语将边缘表达他者化,主流社会得以维护自身秩序的正当性,将对“不 conform”的压制合理化为“维护道德”和“公共卫生”的需要。福柯曾研究精神病院、监狱等制度如何把偏离规范的个体加以隔离和规范,现代社会的话语场域亦扮演着类似角色——报刊与网络言论充当了“看不见的医院和法庭”,对边缘青年的行为进行诊断、审判,剥夺其话语权。总之,大众话语对地雷系等边缘表达的种种简化和污名,并非孤立现象,而是社会行使结构性压抑的一环:将异质性的声音通过嘲讽、恐慌或商品化加以处理,让主流得以不受其扰地延续,在此过程中,对边缘群体的现实诉求和结构性问题则可以被轻易忽视或正当化。
四、展望:拟像社会中的身份疲劳与超越路径
拟像时代的身份演出疲劳。 我们当今所处的高度媒介化社会,正如鲍德里亚所揭示的,是一个拟像横行的社会。在这个“拟像社会”中,符号和形象不再对应坚实的现实基础,而是彼此复制、循环,构成了一个自我指涉的超真实环境。身份认同也深陷于这样的超真实迷宫:个人被迫不断表演、刷新自我形象以符合某种预期的符号模板(无论是主流的职业人设还是边缘的亚文化人设)。长此以往,个体出现了一种普遍的**“身份演出疲劳”。正如戈夫曼理论的批判者所言,当日常生活完全拟剧化,主体便逐渐走向虚空——真实的“自我”被无休止的角色扮演所消解,留下的是一个为了取悦想象中他者的形象拼贴。边缘青年在扮演“地雷系”“Menhera”等角色的过程中,原本期望借此得到认同与归属,但过度的演出反过来也让他们感到虚假与倦怠**:当每一个姿态、每一句话都服务于营造人设和迎合受众,他们难免产生“被角色操纵”的疏离感,仿佛自己只是社交媒体上的一个NPC,而非真正被理解的人。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的他者(观众)也对层出不穷的自我表达感到麻木——当所有人设都被商品化、模式化后,观众很难再从中给予真诚的反馈或承认。于是在表演者和旁观者两端,都出现**“承认机制的危机”**:个人渴望被看见、被接纳,但获得的只是点赞数据和刻板印象式的评论,而非真正的理解或尊重。这可以借用社会学者霍耐特(Axel Honneth)的“承认理论”来阐释:健康的主体认同有赖于在家庭、法律、社会等不同层面获得他人的承认。然而,在拟像化的社交环境中,承认被浅薄的关注所取代——人们关注的是人设符号是否有趣、新奇,却无暇也无意去承认符号背后那个具体而复杂的人。当认同的诉求陷入这种结构性落空时,边缘群体的心理状态无疑会更加恶化,进一步加剧表演和现实的脱节,形成恶性循环。因此,拟像时代的身份疲劳和承认匮乏,不只是边缘青年面临的问题,也是整个后现代社会的通病。
第三条道路的想象:超越主流与表演性边缘的生存结构。 面对上述困境,如何为边缘认同寻找“第三条道路”,成为亟需思考的课题。这条道路既不同于简单地回归主流生活轨道(因许多边缘青年已被主流体系排斥或伤害),也不同于继续沉溺在自我表演的边缘圈层无法自拔。它应是一种中间态的生存结构,容许多元身份以低冲突的方式共存并获得基本的尊严与支持。首先,这需要培育弱连接社群的土壤。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曾提出“弱连接”的重要作用:松散的人际网络可以将不同群体、资源桥接起来,带来强关系圈子内部无法提供的信息与支持。对于边缘青年而言,弱连接形式的社区(例如开放的线上论坛、兴趣小组、临时工作坊等)可以成为他们走出封闭自我表演圈层的踏板。在弱连接社群中,他们既不用像在主流社交中那样压抑个性以求融入,也不会像在原本边缘小圈子中那样陷入同质化的“鄙视链”。松散多元的联系可以给予他们**“陌生人的认同”——一种来自外部的新鲜视角的肯定,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价值不止于某个狭隘人设。其次,需要构建更多非商品化的认同空间**。也就是说,提供一些社会文化场域,在其中身份认同的构建不以市场交换为前提。在这类空间里,人们可以表达和发展自我,而不必将其立即包装成可以出售的内容。例如,社区主导的艺术创作空间、青少年免费活动中心、同辈互助的心理支持小组等,都可以成为“去商品化”的缓冲带。在这些空间中,个体的故事和情感可以被倾听和回应,而不会被当作猎奇素材去炒作,也不要求他们把痛苦变现。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指出,青少年阶段的核心任务是解决“自我认同 vs. 角色混乱”的冲突,稳定的认同需要在社会互动中逐步试错、被承认。非商品化空间正是提供这种安全试错和真诚承认的环境,让边缘青年能探索不同生活可能性,而不必背负表演的重压。再次,完善低结构的支持机制。传统的救助或矫正往往过于官僚和刚性(高结构),如学校纪律处分、司法惩戒或强制医疗等,不仅令边缘青年反感,也难以顾及其个体差异。低结构支持则更灵活、多样,例如匿名咨询热线、线上心理辅导、街头社工定点联系,或者由经验人士(曾经的边缘青年)组成的“同伴教练”网络。这些机制不强制介入个人生活,却在需要时随时可及,以温和而持续的方式提供帮助。比如,日本近年来一些NPO在深夜经营面向漂泊少年的“避风咖啡馆”,提供廉价茶点、临时住宿和倾听服务,让逃家或遭受创伤的年轻人有一个缓冲场所,而不问过多身份,不设繁琐手续。这种低门槛、去功能化的支持,恰恰契合边缘群体的实际:他们往往不信任权威组织,但愿意接受善意且不干涉自由的援手。
制度想象与结构性关怀。 从更宏观的角度,一个包容多元的未来社会需要在制度上做出想象力和变革。或许我们应当考虑构建一些**“中间态”的制度安排**:介于医院与社会之间的心理休养社区、介于学校与家庭之间的青年陪伴计划、介于全职就业与失业之间的弹性劳动项目等等。这些制度的要义在于打破非此即彼的二元划分,正式承认人生轨迹的多样性,将边缘化的人生视为社会光谱的一部分而非异类。例如,探索实施基本收入保障或类似政策,给予每个公民不论其生活方式如何都有基本生活保障的权利,那么那些无法适应激烈竞争、选择另类生活道路的青年也能不至坠入绝境,从而减轻身份焦虑的物质压力。又如,在教育体系中引入多轨道模式,让学业中断、社恐厌学的学生可以通过网络课堂、社区大学等途径以自己节奏完成教育,不让一时的边缘化演变为人生的永久烙印。这些制度上的想象,意在扩展主流的边界,使“主流”本身变得更多元、弹性,从而包容原本被视为边缘的群体。在一个凝聚力强而弹性充足的社会结构中,或许“地雷系”一词终将失去存在的土壤:因为没有人再需要用极端的表演来换取关注,每个人多元的心理需求都能在常规渠道得到回应。在通往这样的未来之前,我们正处于一个充满挑战的过渡期。然而,边缘认同者的探索与挣扎本身,为社会提供了一面镜子,迫使我们反思现有结构的弊端并寻找新的出路。透过地雷系文化兴衰的现象,我们批判既有社会结构对个体的规训与压迫,同时也从中汲取灵感去想象另一种联结与承认之方式。这第三条道路的实践或许困难重重,但唯有开启这样的结构性想象,我们才能走出单一同质的现代性困局,让每个边缘个体都拥有不以表演或隐退为代价的立身之所。
结语
本文的结构性分析试图证明,所谓“地雷系”“魔爪少女”或“男の娘Vtuber”的崛起,并非一场亚文化的偶然风潮,而是社会深层失衡所引发的感知危机与存在焦虑的真实回应。
当制度不再提供可被信任的路径,当社会不再赋予普通人“被完整看见”的机会,当认同只能靠表演来构筑——个体将不得不以“过激”的方式存在,以“消费性角色”换取最起码的注意力与庇护。
我们不应轻率地将他们归入“病”“疯”“奇”“玩”的分类之中,也不应急于将他们归训为“正常人”“可救者”或“对象化的症候群”。相反,我们应在结构层面上追问:我们的社会是否给予了他们除了“归顺”或“崩溃”之外的第三条路?
或许,我们每一个人终将在生命的某个节点遭遇同样的问题:
- 当意义崩塌,我还能相信什么?
- 当标签无效,我要以怎样的方式活着?
- 当他人不理解我,我是否还有权力成为“我”?
请记住:
不要因为你不理解,就轻视;也不要因为你感动,就急于拯救。
理解是一种承认,参与是一种共振,改变是一种缓慢的共同生成。
在这条并不宽敞的时代裂缝里,愿我们都能找到一种不以自我毁灭为代价的活法。
参考文献:
- Goffman, E.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Doubleday.
- Judith Butler. (1990).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Routledge.
- 福柯(Michel Foucault).(1975). 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
- 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81). 拟像与仿真(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 虎嗅青年文化组. (2025). “魔爪泡饭”:日本厌食文化找上中国少女
- 维基百科:“女番长”条目
- 机核网:平成日本青年文化年谱(1983-1994)
- 《新闻学研究》:罗彦杰 (2018)〈污名报导之流变〉